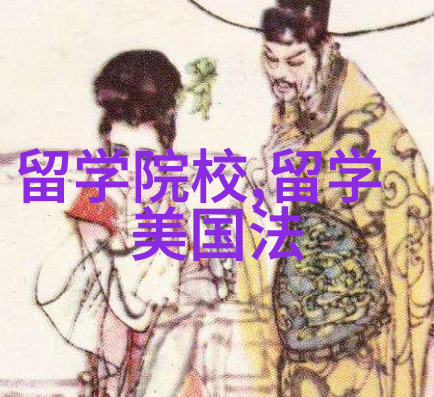我曾在加州的夏日中体验了西方的远足,那些青山给予我的印象至今难忘。十七岁时,我第一次踏出了国门,来到加州与一家人相聚。那里的自然风光让我对“远足”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,但当时我并不喜欢这种活动,只好忍着炎热,在荒无人烟的丘陵地带走上数小时,心情枯燥乏味。我义父却总是说它很有趣,我心里想,这哪里有趣啊?

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学会了欣赏远足,它不仅是一种运动,更是一种接触自然、挑战自我的方式。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古人会把水和山比作智慧和仁德。尽管我从未真正涉足中国的五岳或黄山,但每次远足,都让我更加珍惜这份简单而纯净的心灵体验。
后来,一次与朋友去香港南丫岛的远足经历,让我意识到这种活动并非总是轻松愉快。在那片充满危机感和迷茫的大自然中,我们两个土生土长的人默默前行,没有多余的话语,只能依靠内心坚韧度过那些艰难时刻。但随着旅程不断进行,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,从急躁转变为慢性追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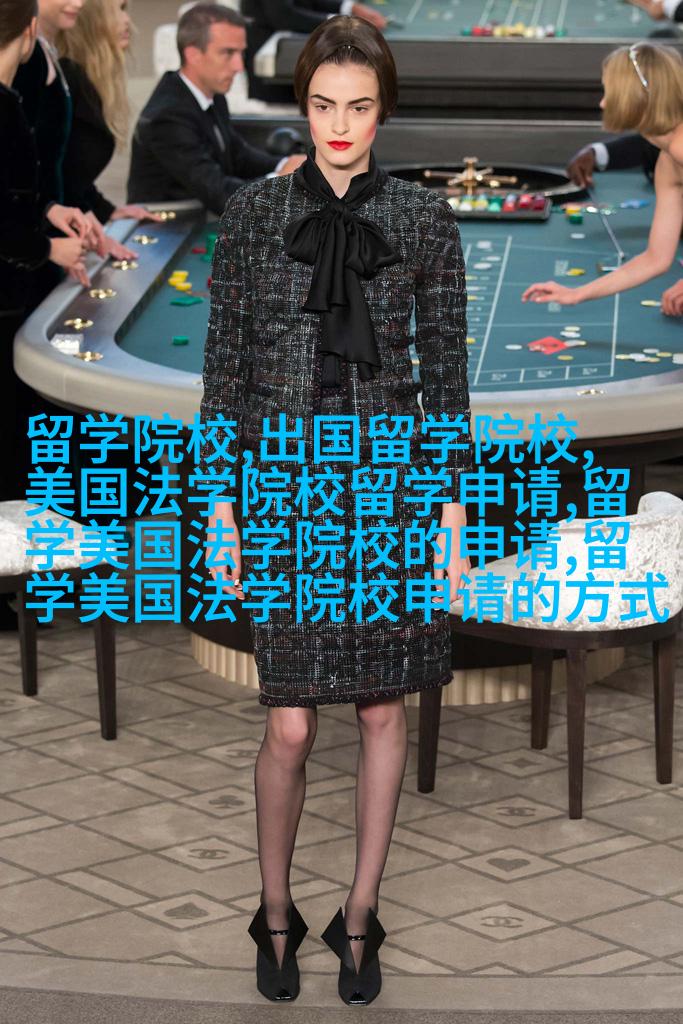
再后来,在婺源的一次午后的雨天,我们面临了一段漫长且泥泞不堪的小路,每个遇到的行人都安慰我们距离目的地只剩五公里。这让我们既鼓舞又沮丧,最终,当我们看到目标村庄轮廓出现时,那份喜悦之情是无法言喻的。在这样的经历中,心理鼓励成为了彼此间唯一可依赖的事物。
毕业后回到北京,我偶尔还会跟一些老友一起去爬郊外野长城。这些高手们深谙此道,他们在山陵之间游走,而我则渐渐学会如何调节自己的状态,让自己能够享受这场顶风漫步般的情景。在他们眼里,即使是在秋意浓重的时候,也是我如同帝王一般挥洒自如。

然而,在河北三界碑一次险峻下坡过程中,我差点失去了平衡,幸运的是队友及时救援。如果不是她们经验丰富的手腕,那可能就一切皆无。当回忆起这一切之后,我才意识到,无论何处旅行,无论何种冒险,都需要一种对自己身体状况超敏反应,以及对于环境适应性的学习。而最重要的是,与他人的关系处理,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处理,这两者都需要努力才能做得好。
直至今日,或许仍是我更爱海洋的人。但那些青山,不怒自威,其凛然之气也常让心生惧意。而与它们多年的缘分,却教会了我克服恐惧,为进步而笑,同时也让我的视野扩大到了新的层面。